岁月悠悠流淌,腊月翩然而至。年,又近了,年味渐酣,依稀可感。不知从何时起归家便成了萦绕在人们心尖上的念想,孩童时的年味让人怀念,长大后的年味让人向往。沿着记忆的河流,用一些怀旧的思绪,去追寻那些字字珠玑诗文里的年味。去人间烟火处,闻一闻年的气息,感受一下年的气象万千,释放一下内心的欢愉。

过了腊八,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年气儿也就开了。人漂泊的时间一长,就会时常想家,尤其是过年这个时候。年味渐浓,厂区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愈发的温馨喜庆,归乡游子瞧着喜庆的灯笼涌上心头的是期盼和幸福。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是掸尘扫舍、祭灶的日子。我刚睡醒,母亲就开始张罗着要打扫卫生。在八十年代,陕西一带农村还多是土坯房,砖木结构的房很少,农村人烧的是柴火,烟熏火燎,一年下来,烟熘串子吊得老长,上面布满了灰尘,不打扫一下,实难见客。我和父亲负责打扫卫生。母亲则把家里的床单、被褥、衣服都洗了,一绳一绳晾出来。厨房的案板上也早已摆满了丰盛的祭品,母亲点一对烛,上三根香,虔诚地磕头。一直忙到晚上兴许是肚子饿了,辗转难眠,在床上“翻烙饼”,心里仍惦记着那些祭品,只盼着天快些亮。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备年货。爸爸妈妈负责买菜、买鱼、买肉,我就负责买一些小的物件,像窗花、生肖年画、糖果花生等。过了小年,日子便快了起来。县城里人摩肩擦踵,赶集的人密不透风,吃的、穿的、用的不停地往回买。母亲买了一大堆,结果还是有东西遗漏了,或者突然想起又差一样东西没买,折身再往集市上跑,照面遇上熟人,总要互相问“你年货办完了没有?”。
年三十村里的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开始响起。母亲就更忙了。煮肉、蒸馍、炸油品、剁饺子,恨不得一天能当两天用,其刀砧之声,远近相闻。厨房里的热气,从窗户缝中挤了出去,把院里的空气都给搅香了。我则帮着母亲打下手,弟弟帮着父亲挂灯笼,贴对联、将准备好的窗花、年画贴在窗户上。
除夕,月穷岁尽,要守岁熬年。家里灯火长明,丰盛的菜品摆了一桌,吃过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春晚开始包饺子,我负责擀皮,爸爸妈妈包饺子,弟弟在一旁玩耍,一家人其乐融融,平淡中夹杂着幸福。包完饺子,就到了我们小朋友点燃烟花棒的时候了。这时候我一般都不舍得快快点燃,就像有好吃的想留到晚一点再吃一样。我看着小朋友们甩着仙女棒笑着、跑着,就像带着流星穿梭在人间一样,好看极了,也热闹极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浓浓酽酽的年味到了巅峰,一台电视,一台春晚,一家人围着,歌曲唱着年味、舞蹈跳着年味、小品说着年味,难忘今宵,只留年味在心头缠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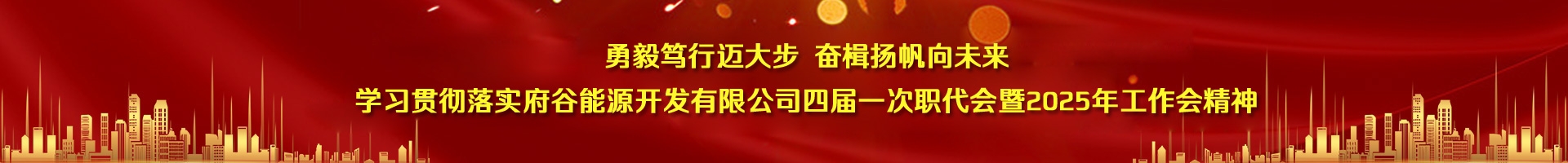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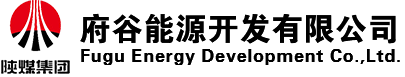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