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仿佛是我生命中一株经久不衰的木槿。当我拿起书本,我得以心静;当我心静之时,我便拿起书本。我常常游历于书籍这片辽阔的海洋之中,漫无目的,悠闲惬意。最近难得闲适,便又拿起《尘埃落定》,细细读罢,有新体悟,也有新收获,可谓常读常新。
关于《尘埃落定》,首次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她,其实也历经了许多的风风雨雨,算得一位“中年老者”。作者阿来也以独具匠心的题材和沉稳的笔触,通过描写一个土司傻儿子的耳闻目睹向读者展示了奇幻的藏族风情与当地土司制度的神秘与衰亡。同样,这也让阿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犹疑暧昧的文坛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授奖致辞中,评委们这样说到:“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诚然,我们可以见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人,阿来不遗余力地冲出思想壁垒,将他的血脉情感与思维家园一一结合,历经数年呕心沥血,终于在一九九四年定稿,打造出了一部属于藏族人民的不朽传奇与民族秘史。
在《尘埃落定》这本书中,给我直面且最为猛烈的冲击当属旧制度的尘埃。罗曼罗兰曾经说过,强制的社会制度不会是永存的。这也揭示了旧时藏族土司制度的历史悲歌。当我读罢合起书本,悲恸之感直涌心头,内心意难平。这使我联想到了《百年独孤》的沧桑与无力感。作者阿来更是有意为之,以主人公“傻子”的死亡宣告了这一旧制度的生命终结。在后来的《空山》中,阿来更是延续了这一炙热手感,从结构与故事多点升华,讲述着藏族历史长河中的坎坷与离奇。
其次,让我眼前一亮的当属“我”——麦琪土司的傻儿子。初读文章就使我兴致盎然,我常常思忖这其中是否存在着作者童年的些许阴影抑或是作者内心的某种心绪与神往。总之从一个傻子作为切入点,这实在为一种尝试。但在中国当代文坛中,这也并非没有前例。在贾平凹先生的《秦腔》中,也有一角似疯非疯,即为“引生”。引生的病态是带有哲理与象征意味的,他是作者高度凝聚的、被抽象出来又具象化了的人物。他的存在反映了某种被理性分析所窥视了本相秘密的现实生活,他不仅是人性的体验者,更是一个带有特定文化烙印的先锋者,成为一种超脱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生命符号。正如哈姆雷特所言:“疯狂的人往往能够说出理智精明的人所说不出来的话”。
同样,在《尘埃落定》中,“傻子”也并非纯傻。在书中的一些桥段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也有聪慧的一面,他在某些紧要时节的想法与见解,甚至超越了一众“聪明人”。在我看来,他具有较为缜密的心思并且清晰地知道目标所在。因此按照我的理解,傻子其实是一个“聪明”的傻子。除此之外,傻子也是一个优柔软弱、性情温和的俗人,这其实与我们不尽相同。他更像是一个特殊背景下的历史写照,将麦琪家乃至藏族世界的历史娓娓道来,犹如流水淙淙,平和、舒缓,却又不失本色,让人不禁赞叹起历史的厚重与缥缈。他比塔娜更奇妙更复杂,我甚至一度读不出他的内心所思以及他的怪异之举。譬如看天,譬如预知未来。同时对他的温柔和善良表示由衷地赞叹。但对待感情,他则更像一个傻子,一个彻彻底底的傻子。他可以一直深爱多次背叛过自己的妻子而不计前嫌。当然他也有动摇的时刻,但这些念头终会被他扼杀于襁褓之中。我不明了他到底是傻还是聪明,似乎有些茫然。
关于塔娜,她让我满足了对美的一切遐想,作者阿来倾尽所有,将其描写得风姿绰约、沉鱼落雁。其中有一段描述这样写道,“她穿上缎子长袍,晨光就在她身上流淌。别的女人身上,就没有这样的光景。光芒只会照着她们,而不会在她们身上流淌”。但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最终竟成为了一个傻子的妻子,让人不难觉出这其中的几分荒诞与虚幻。但随着阿来的设计与布局,我们发现,其实塔娜对于傻子而言,并不足以让我们神驰,反之让我们感到怜惜与同情。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塔娜的人设——滥情且高傲。她凭借着自己出众的容貌处处留情,同时又常常轻视自己的傻丈夫,这一微妙的安排也为文本增添了不少神奇色彩,使得这位主人公的生活变得富有传奇,同时又略显悲剧。
我总觉得,塔娜应该是一位真善温纯的女子,不应有过多瑕疵。譬如《受戒》中的小英子、《边城》中的翠翠,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这些角色要么真切,要么忠贞。反之塔娜则与这些人物形象大相径庭,她不乏美色的同时又大方露骨,这使我联想到了《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尽管他们都妖娆妩媚,但终因其种种过失而落得悲剧收场,这也实在让人惋惜。但或许,这即是阿来想要向世人展示的本真面貌,让塔娜的形象更为丰厚饱满,变得呼之欲出。因而,我以为,一个真实完整的人物形象就该有这些瑕瑜是非,不然塔娜,甚至这本书,都会缺失完美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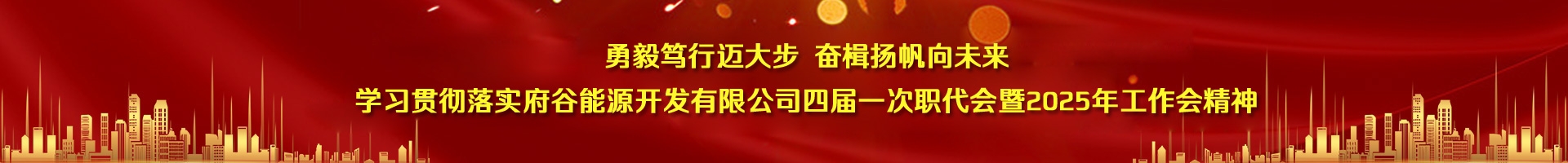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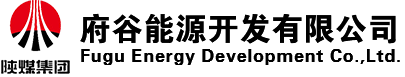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