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当读到艾青的这句诗歌时,一股别样的情愫瞬间让我回想起以前帮爸妈做农活的场景,思绪久久不能平复。是的!我爱这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她就像一杯烈酒,让我陶醉其中;她也像一首老歌,让我如痴如醉;她更像一杯浓浓的香茶,让人回味无穷。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是路遥形容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原上的人民的真实写照。陕北的季节是四季分明的,地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这里的农时是“十年九旱”,农情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用当地的一句话形容就是“收的连籽都不够”。可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庄稼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倔强地忙碌在田间。儿女为了生活远离故土奔波在远方,大多是帮不了父母多少忙的,他们更不会把庄稼人辛苦的一面呈现给子女,不愿意跟随儿女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大厦里,也许是为了生活,也许是出于对这片扎根地方的情怀,喜欢端着饭碗和乡里乡亲拉拉话。以前我不太懂,困扰我多年,直到这些年漂泊在外,为人父,为人夫,才明白城市再繁华,也割舍不断故乡,故土难离,乡情难断,就像树上的叶子走过春秋季节,冬季回归大地一样,人生亦是如此。
在“春雨贵如油”的日子里,人们抢着节气去播种。今年开春回家帮父母播种,一大清早,母亲早早起来用窑洞里的“锅灶”开始做饭,农村的早晨空气清新,天高气爽,几只黄鹂在树间戏耍叽叽喳喳地叫着,鸡窝里的几只公鸡时不时打几声鸣……”,邻居家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泥土的清香更是让人心旷神怡,母亲做饭时飘出来的袅袅炊烟飘在天际,形成一幅优美的风景画,让人流连忘返。母亲饭熟的声音打断了我,望着发髻已有几许白发的母亲,额头皱纹也深了许多,心里真不是滋味。小的时候盼望长大,可长大后才知道人生是一场不可返回的旅程,狼吞虎咽地吃着母亲做的“山药丸子和鸡蛋炒粉条”,泪水偷偷地打湿了眼眶,母亲以为我噎着了,笑“骂”我的吃相,多么希望永远被母亲这样“骂”下去。父亲不善言语,给予的爱就如黄土一样深沉而又博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说的就是父亲这辈人,饭后一整天和父亲把希望的种子深埋在这片黄土地里,期盼着种子在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有个丰收光景。
夏天的日头火辣辣,晒得滚烫!人们头顶草帽,搭着湿漉漉的汗巾、赤脚疾行在沟沟峁峁的田地里,用力的挥舞着锄头除草,生怕有一颗杂草抢夺了庄稼的水分。遇到久旱,人们会举行“祈雨”活动,家家户户平摊出钱,请戏曲班在村里唱大戏,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大人们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互诉着家长里短,时而低声哭泣,时而哄堂大笑。与此同时,娃娃们也迎来了“难得”的快乐时光,因为亲人欢聚一堂的同时都会给小孩们带些玩具或是小零食,因此小孩们巴不得村里天天唱大戏。
秋季是检验一年是否丰收的季节,对于务农的庄稼人来说至关重要。今年无疑是丰收的,放眼望去地里绿色开始泛黄,乡间小路已失去绿色,可以看到挂到树间红彤彤的枣子,尝上一颗沁入心田;成熟的谷米穗子泛着金黄,在秋风中摇曳,仿佛在欢笑着庆祝丰收;阳光下的向日葵整整齐齐排列在梯田间,仿佛整装待发,等待“领导”的检验。遇到过路的行人或者孩子,庄稼人会送上枣子、苹果、梨等,热情而又淳朴,你可以看到每个去田间收庄稼的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冬季的陕北,寒冷而又干燥。在这种天气下,庄稼人也是闲不住的,去沟里将晾干的玉米秸秆运回来喂牲口或者做取暖使用。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陕北农村主要以石窑洞为主,冬季的农村是要“烧炕”的,农作物秸秆是最好的燃料,经济又实惠。中午天气回暖一点便将牲畜的粪便从圈里掏出来晾干,然后拉运到地里,为明年播种庄稼准备肥料,当然在大雪纷飞的天气也会三五相约,在小红桌上摆上一壶老酒、炒上几个热菜畅饮一番,这大概就是他们独有的“享受”和庆祝方式。
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游子数不胜数,不论走多远都始终难忘故土,想念走过的山沟、树林,更忘不了家乡的人儿,多少次魂牵梦绕地回到故土。如今,又已到深秋,那些仍在外漂泊的人儿,如果乏了、倦了或是疲了,不妨回来再走一走以前走过的小路,跨一次以前玩过的小河,望一望以前看过的山沟沟,爬一爬以前绕过得山梁梁,更要为那年迈的父母捧上一杯热油茶,认认真真听听他们想要诉说的每一句家常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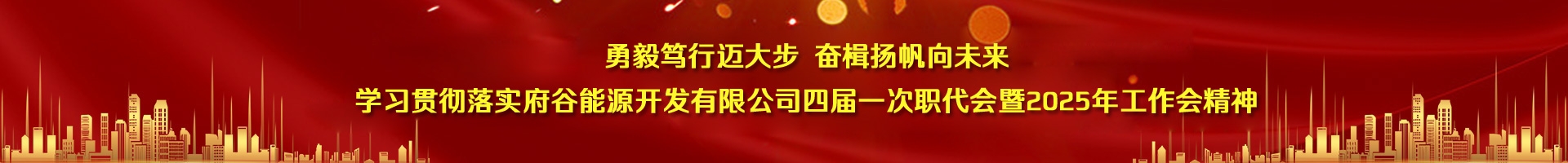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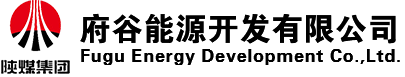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