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辈子就是种地受苦劳碌的命。这不,就在他自我感觉体力不济,把他和我奶奶的地一分为二给两个儿子种,让儿子们赡养他们,他完全可以悠闲自在地在家中怡享天年的时候,他却又到我们门前河滩边拾掇出了几块边角地种上了玉米、山药、向日葵、旱烟;其中,种得最多的是旱烟。旱烟的历史据说非常悠久,我却没兴趣去考证,我估计爷爷也不知道,他只管种和抽。旱烟的种植,据说流程繁多,技术含量也高,外行是种不出来的,但我儿时所见的是我们那儿的人家几乎家家都会种植旱烟。当然,我并没有留心过种旱烟的人是如何去下种、匀苗、定矩、尖、打岔,是如何的辛勤。我只记得爷爷种旱烟的时候,是上一些牛粪、驴粪之类的肥料,长出的烟叶,没有化学物质污染,应该是绝对的绿色食品。

爷爷一生务农,在我们村里绝对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尤其是他种的旱烟,在方山周围是小有名气的,我就见过有好几个爱抽旱烟的老汉,到一辈子再未做过其他买卖的爷爷这里买旱烟。《平凡的世界》里,少安少平的父亲孙玉厚老汉也侍弄得一手好旱烟,那部分内容我看得特别仔细,在惊叹路遥先生观察生活细致入微、描写人物出神入化入木三分的同时,我坚信他身边肯定有一个像我爷爷这样的生活原型。爷爷的烟锅子是他的命根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离身不离手。我们小的时候,兄弟姊妹一起玩,有一回不知怎的,看见爷爷破天荒百年不遇地竟然把烟锅子忘在炕楞边,说不上是胆大包天却也是鬼迷心窍,我们竟想起把他的烟锅子给藏了的主意。其实也就是藏到了爷爷住的屋里脚地上水会和菜会之间的空隙里,不过那地方光线暗。不一会儿,爷爷一头撞进门,左瞅右看,找了半天找不到,看我们几个在一边鬼鬼祟祟的样子约莫这是我们给他藏了,便把个眼瞪得像灯似的抡拳过来,吓得我们几个屁滚尿流叽哇吵乱抱头鼠窜,最后还是奶奶给找到才免了我们的皮肉之苦。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烟锅子就是那一杆:烟锅头有小酒盅那么大、圆形,是铜的,能从那颜色上看出来;烟锅杆是用槐木还是杏木枣木做的已看不出来,因为通体成了黑色;烟嘴子又是白铜的,被口水浸泡得也快要发黑。爷爷抽烟时,点着了烟锅头,先只见那么一星期甚至是一丝红光,让人直担心那点红光会熄灭。可他却不紧不慢着烟嘴抽一口吐一下,抽一口吐一下,就像一个品酒的人把个品位拿得十足!然后是越抽越快、越抽越快,伴着咝咝的吧嗒声,倏忽间,烟锅头已是通体通红。然后又是越抽越慢,越抽越慢,抽一口呼出一口长气,抽一口呼出一口长气,烟锅里先是一明一暗、一暗一明,最后黯然失色,烟嘴里也不再有烟冒出。这时爷爷就像一个梦游忽然醒来的人,身子似那么一抖,就听“吧”的一声,烟锅头里的烟灰已被磕了出去。而抽完一锅子烟的爷爷,微闭的双目并不急于睁开,就那么静静地呆一会儿,然后才起身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爷爷的这一杆烟锅子最令我称奇的是他磕烟灰时“吧”的那一声是那么清脆、让人感到是那么有力,可一尺多长的烟锅杆却从来没被磕断。我可是亲眼见过几个老汉在人多势众面前磕烟锅把烟锅杆磕断,惹得众人哄堂大笑的尬情景的。当然这是爷爷大多数时间一个人自己抽烟时的情景,遇到人多聚在一起边拉闲话边抽烟,那就是又一番情景了。大多时候是先自己挖着自己烟锅杆上吊着的烟袋里的烟叶抽,然后就是我敬让着你到我的烟袋里挖一锅烟,他又回敬着让你到他的烟袋里挖一锅烟,然后众人就散坐着有时围坐着吧嗒吧嗒抽开了。缭绕中,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寒来暑往、春种秋收,高一声低一句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或者一天劳作下来的疲惫不堪,甚至邻里之间的磕磕碰碰、恩恩怨怨,都在那缭绕的烟雾中云开日出、烟消雾散。
可惜爷爷的那杆烟锅子在他去世后不知被丢到了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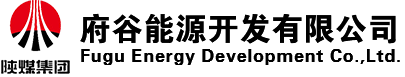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