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年货的记忆,是从腊月宰猪开始的。
从我记事起,陕北农村人家,没有不养年猪的。一般的人家是春天抓猪仔,喂上一年,不管它长多大,进了腊月门,都会被宰掉。猪挨宰时嗷嗷叫着,乌鸦闻着血腥味,呀呀叫着飞来。不过好的屠夫,会让它连一滴血都尝不着。血被接到盆里,灌了血肠吃了!猪被大卸八块后,敞开肚子吃顿肉,然后把余下的作为年货,存在仓房的大木箱里。怕它风干了味道不好,人们在储肉箱里撒上雪。
过年的餐桌上光有肉是不行的,年夜的餐桌上,还必须有鸡,有鱼,有豆腐,有苹果,有芹菜和葱。鸡是“吉利”;鱼是“富余”,豆腐是“福气”,苹果是“平安”,芹菜是“勤劳”,葱则是“聪明”,这些一样都不能少!

在过去,年货采购是春节前的重头戏。那时,餐桌上的鱼大多是冻鱼,草鱼、鲤鱼、鲈鱼等常见品种,便是家家户户能买到的年货。这些冻鱼被整齐码放在集市的摊位上,带着几分冰天雪地的凛冽气息。做鱼时,老一辈总会千叮万嘱,千万不能剁掉头尾,只因“有头有尾”是对来年生活的美好祈愿,寓意着年景顺遂、圆满。若是想要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摆上一条鲜鱼,那可得看运气。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鲜鱼就像稀世珍宝,若能碰上,那便是新春里最大的惊喜。
比起鲜鱼,豆腐就很容易获得了。我们小镇有两家豆腐坊,得到豆腐除了用钱,还可用黄豆换。一般来说,换干豆腐,比水豆腐用的黄豆多。男人们扛着豆子去豆腐坊时,你从他们肩上袋子的大小上,就能看出这家过年需要多少豆腐。莹白如玉的水豆腐进了家门,无非两种命运,一种切成小方块进了油锅,炸成金黄的炸豆腐片,另一种则直接摆在户外的木板上,等它们冻实心了,装进布袋,随吃随取。
除夕宴上的葱,是深秋储下的。葱在我眼里是冬眠的蔬菜,它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看似冻僵了,可是进了温暖的室内,你把它扔在墙角,一夜之间,它就缓过气来,腰身变得柔软了!又过几天,它居然生出翠绿的嫩芽了,冻葱变成水灵灵的鲜葱了!至于芹菜,它也来自田园,不过它与葱不同,要是挨冻,就是真的冻死了!芹菜秋天时割下来打捆,下到户外的菜窖里。两三米深的菜窖,储藏着土豆、萝卜、大白菜等越冬蔬菜,芹菜就和它们同呼吸共命运了。不过芹菜没有它们耐性好,叶片很快萎黄,幸而它的茎,到年关时没有完全失去水分,仍然能做馅料。
年夜饭中唯一的冷盘,就是苹果了。苹果可用鲜的,也可用罐头的。我们那时更喜欢罐头的,因为它甜!去小卖部除了买苹果,我们还要买烟酒糖茶,花生瓜子,油盐酱醋,冻柿子冻梨。最重要的是,买上一新碗新盘子,再加一把筷子,意谓添丁进口,家族兴旺。
在置办年货上,家中的每个人都会行动起来,各司其职。主妇们要去小卖部扯来一块块布,求裁缝裁减了,踏着缝纫机给一家人做新衣。缝纫机上的活儿忙完了,她们还得蒸各色新年干粮,馒头、豆包、糖三角、糕角等等。男孩子们负责买鞭炮,买回后放到热炕上,让它干燥着,这样燃放起来更响亮。他们还要帮着大人竖灯笼杆,买来彩纸糊灯笼。
小年前后,我会和邻居的女孩子搭伴,进城买年画。好像女孩子天生就是为年画生的,该由我们置办。小镇离城里十几里路,腊月天通常都在零下一二十摄氏度,我们穿得厚厚的,可走到中途,手脚还是被冻麻了。母亲嘱咐我,画面中带老虎的不能买,尤其是下山虎;表现英雄人物的不能买,这样的年画不喜气。她喜欢画面中有鲤鱼元宝的,有麒麟凤凰的,有鸳鸯蝴蝶的,有寿桃花卉的。而父亲喜欢古典人物图画的,像《红楼梦》《水浒传》故事的年画。母亲在家说了算,所以我买的年画,以她的审美为主,父亲的为辅。这样的年画铺展开来,就是一个理想国。
买完年画,我们会去百货商店,给自己选择头绫子、发卡、袜子,再买上两副扑克牌。任务完成,我们奔向百货商店对面的小吃店,一人买一根麻花,站着吃完,趁着天亮,赶紧回返。我们嘴里呼出的热气,与冷空气交融,睫毛、眉毛和刘海染上了霜雪,生生被寒风吹打成老太婆了!不过不要紧,等进了家门,烤过火,身上挂着的霜雪化了,我们的朝气又回来了!
而今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岁月让我有了丝丝缕缕的白发,但我依然怀念小时候过年的情景。虽然我们早已从小镇迁到小城,灯笼、春联都是买现成的,再不用动手制作了。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实际,可也越来越没有滋味,越来越缺乏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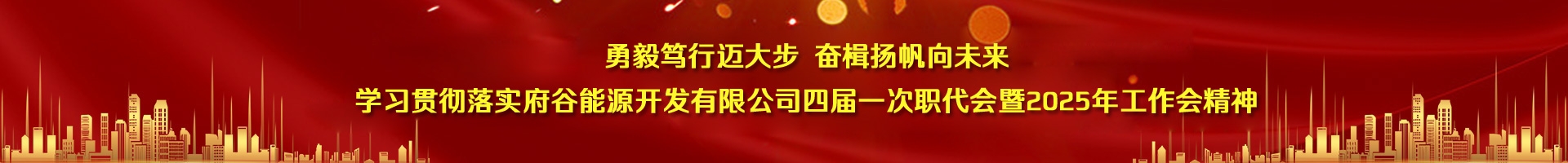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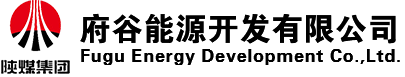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