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的天色像被揉皱的棉纸,晴时泛着暖金,阴时蒙着灰蓝,偶有黄风卷着细沙掠过,把季节的边界吹得模糊不清。电话里爹娘总说“等天暖些回村”,那带着乡音的絮语,像一根无形的线,将我心里的牵挂绕成茧——那座黄土坡上的小山村,是爹娘扎了大半辈子的根,也是他们藏在皱纹里的执念:开春要翻的菜园土、硷畔待剪的枣树枝、山洼里该施的农家肥……桩桩件件,都是刻进骨血里的乡思。
生活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前行着,又恰逢工作休假,于是乎头顶着天际的启明星,拥抱着暗夜急匆匆赶往家中。当天际泛出一抹鱼白、城市还处在喧闹前静谧的时空中赶到家中,娘看到我时呈现出惊愕,同时喜悦从娘的脸上迸发出来,轻声细语交谈几声。我去看了看熟睡中的爹,自从手术之后明显整个人苍老许多,以前高大健硕的身体已不复存在,一根根青筋凸出,纵横交错,发髻线明显上移了许多。我与爹一直不善于沟通言谈,直到上次在病床前整日整夜的陪伴才拉近许多。随后轻掩门离开,催促娘再去睡一会儿,天色还早。妻子和孩子还在熟睡,端详着熟悉再不能熟悉的面孔让人心生爱惜,挨着他们躺下休息一会儿,等着他们醒来后要带着他们走一趟特殊的“寻根”之旅。
窗户上刺眼的光芒照射在屋内,再睁眼屋内空落落只剩下我一人。娘在灶台前搅动小米粥,蒸汽氤氲了窗上的红窗花;爹握着扫帚,把昨夜的尘土聚成小堆,扫帚划过青石板的沙沙声,和孩子们的笑闹声织成一片。
吃过早饭后,简单地收拾了一番,便带着家人踏春去了。走在熟悉的道路上,映入眼帘的依然是冬暖夏凉壮观的窑洞群,大体有土窑洞、石窑洞,以及平地垒起的砖窑,窑洞周围簇拥着几种树木,由于地处干旱半干旱之地,种类并不多。山坡上还有一些柳树,垂柳依依,跟随风儿摇摆,仿佛在欢迎久别归家的人儿,路径上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黄灿灿的花朵,给黄土高坡注入一抹新奇,内心充满温暖。石头山下,山涧的小河早已恢复“嬉闹”潺潺的奔流在崖间,穿梭到一眼望不到的地方。
爹直奔果园,粗糙的手掌抚过杏树枝,指尖掠过花苞时格外轻,像在摸孙儿的脸。他教我修剪杂枝:“树要修,人要琢,懂得舍,才有得。”孩子则是安静地聆听爷爷的教诲,明白“春”是希望的季节,懂得吃食“粒粒皆辛苦”。阳光穿过新抽的嫩叶,在他佝偻的背上织出光斑,忽然想起儿时他扛着锄头在地里的模样,原来岁月早把教诲种进了每一寸土地。
夜幕降临,启车返程,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爹娘的身影渐渐缩成两个小点,却始终在塬上立着,像两棵守着根的老枣树。夜风卷着熟悉的土腥气扑进车窗,忽然懂得:家乡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是藏在父母白发里的守望,是刻在孩子掌纹里的来处,是无论走多远都能暖透脊梁的那缕炊烟。
春日的风还在吹,明天或许会晴,或许会雨,但此刻,塬上的星子很亮,老窑的灯还暖,而我们,永远有归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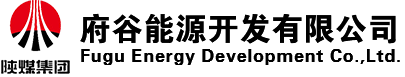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