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八九年,父亲从外面推回来一辆崭新的飞鸽牌“二八大杠”,引得村子好多人来家里观看,那些小孩子拥挤在我家里,想摸这“神器”的手和那羡慕的眼神,让我在人群中感受着无限的骄傲与得意。
乡间小路上,穿着花衬衣的我坐在“二八大杠”的大梁上,父亲扶着车把手的双臂刚好环绕住我的小小身躯,他蹬踏板的腿脚是轻盈的,我的嘴角是上扬的,道路两旁的花和树,是鲜活翠嫩的,连夹杂着黄土味儿的空气都是香甜的。远远地,我看见前面有个也骑着“二八大杠”的男人,他车子上挂着的笼里掉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告诉父亲,他加快速度追上去,我们从路上捡起来那秤杆,使劲朝着前面那人喊:“哎~等一等,你的东西掉了。”
在80年代,父母种着的几亩地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开销,三个孩子都要上学呢。为贴补家用,每天清晨五点多,一声哨音划破乡村的宁静,父亲开始了在村子里收羊奶的业务。上午九点多,他便结束当天的收购,要去奶粉厂交奶了,奶粉厂在相邻的镇子,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父亲用绳索将两个铁皮桶子绑在他的“二八大杠”车座子两边,在熟悉的路线上每天一个来回,晴天平路处骑着走,雨天或烂路推着走。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二八大杠”沾满泥巴,特别是车轮和护板中间,几乎被黄泥塞得满满当当,怏怏地颓在院子里。母亲脸上怒气未消,嘴里唠叨着,抱怨着,“地里活儿几乎都给了我,交个奶到现在才回来,看把车子弄成啥?”父亲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只是低头清理他的车子。不用说,父亲又抄近道去奶粉厂了,那条所谓的近道儿,是引黄工程的水渠,虽然能直线通往奶粉厂,但用“二八大杠”驮着两桶上百斤的羊奶在雨后的渠沿上行驶,难度可想而知。不知道父亲独自推了多久,黑色的千层底布鞋在泥泞里打滑过几次……
一九九九年,父亲骑着他那“二八大杠”到学校给我送生活费,我看着那辆和他并肩作战了多年的“伙计”,第一次感觉到它有些岁月的痕迹了。那天秋风有些冷,我望着父亲从学校门口离开,想起朱自清的《背影》里,那个穿着黑布大马褂的背影,鼻子微微一酸。
二〇〇三年,我要去十公里以外的镇上读高中了,父亲要把它的“二八大杠”给我用,我不情愿地说:“人家现在时兴轻便自行车了。”父亲母亲在商量后,给我重新买了一辆轻巧的自行车,专用于我每周上下学。
后来,我考上大学,飞出那个小小乡村,多数假期也被我用来勤工俭学,很少回去。再后来我工作,和家乡亲近的日子越来越少,“二八大杠”不知何时悄然退休。
二〇二五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回到这个角角落落都充斥着童年记忆的家乡,孩子们对这个停放在老屋角落里的老物件儿充满好奇,吵闹着要骑一下,父亲担心他们没经验,怕摔了,便自己骑车载着外孙玩。父亲的腰背不再如往昔那般坚挺了,但沧桑的脸上浮现出和当年一模一样的笑容,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我久久伫立在那,任思绪飘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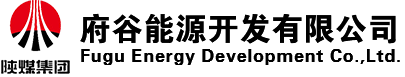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