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九月的风裹着凉意悄没声儿来,转眼又到了秋深的时候。点开老家的监控,院心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得满院都是,层层叠叠铺成金毯子,风一吹就簌簌地动,每片叶尖都沾着秋雨的潮气,泛着润润的光。连着下了几天雨,整个村子都浸在朦胧雾气里,远处的崖坡、近处的窑洞都晕着淡墨色,像幅没干透的水墨画——我明明在千里之外,却像能伸出手触到那股清润,混着黄土地的腥气、草木的嫩香,一下就漫到心口。

岁岁年年轮着转,我离开故乡这么多年,心里头的那个世界,却总被老家的烟火填得满满当当。偶尔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目光总在那所小学上停留很久。如今它早成了一排破败的窑洞,墙皮剥落在窑洞口积成薄土,可每次看着那些残垣,耳边就像又响起放学的钟声——不是脆生生的,是撞在崖壁上绕着圈的回音;还有伙伴们追着跑时,裤脚扫过墙根荒草的窸窣,叽叽喳喳的笑闹声裹着黄土味,怎么都散不去。
校门前的路还那样宽宽地铺着,站在路中间往对面望,就能看见爷爷家的窑洞。小时候,爷爷蹲在窑前抽旱烟,总指着窑洞下方崖壁上那些黑黢黢的洞说:“这是当年乡亲们躲日本人,一凿子一凿子挖出来的。”我凑过去看,石壁上的凿痕还嵌在里头,风灌进洞里会呜呜响,像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崖底下藏着不少草药,十二三岁那年,我跟着邻居家的孩子去挖,小锄头刨得手心发红,指甲缝里嵌着野胡麻的土黄色,傍晚回家时,竹篮底还沾着崖上的青苔,可心里头满是欢喜,连累都忘了。
爷爷家对面的山很高,山顶上长着棵杜梨树。到现在我都记得,爬树摘杜梨时那种又爱又怕的滋味——踩着歪扭的树瘤往上爬,枝杈间的马蜂嗡嗡绕,停在梨叶上时,我连呼吸都要放轻。摘下的杜梨咬一口,酸水顺着舌尖漫开,可我舍不得扔,揣在衣兜里捂热了再吃,那点甜就慢慢从心口漫出来,比啥都好。
回忆像院角的槐叶,落了一层又一层,风再大也吹不散根里的香。这片黄土地虽皱着纹,却把日子里的暖都埋在了窑洞里、山崖下,守着我最初的快乐和牵挂。童年早已被岁月拉远,可每每想起那片山、那些窑,心里还是软的——故乡从来没走,就立在记忆里最暖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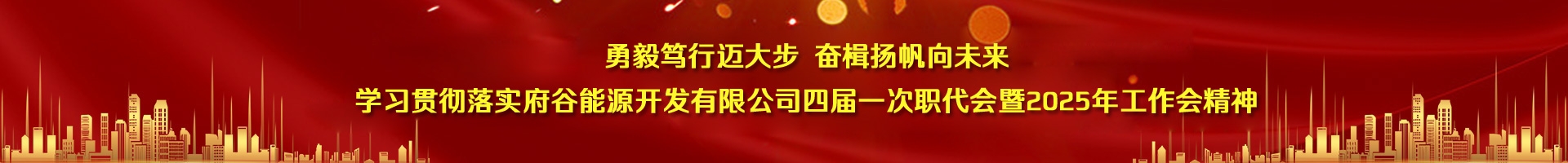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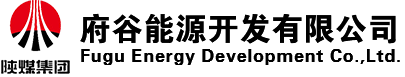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