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秋冬之交,总忍不住想起老家富平的柿饼——那不是普通的果干,是秦岭北麓的阳光、石川河的水汽,还有妈妈布满老茧的手,一起揉出来的甜。打小在富平长大,见惯了漫山遍野的柿树,也记牢了一句话:“世界柿饼看中国,中国柿饼看富平。” 这不是自夸,是每一颗柿饼都藏着的底气。

富平的柿树,多长在塬上。秋末冬初,柿子红透的时候,漫山遍野像落了一场胭脂雨。不是所有柿子都能做柿饼,得选“尖柿”——果形周正,皮儿薄,肉儿厚,咬一口甜得能流蜜。妈妈总说:“做柿饼要等‘霜打’,霜一落,柿子的甜才沉得下来。” 她会带着我去摘柿子,竹篮挎在臂弯里,踮着脚够树梢最红的那一颗,柿子蒂“啪”地断开,带着新鲜的柿香,往篮子里一放,就能压出浅浅的汁儿。摘回来的柿子不能直接晒,得先“削皮”——妈妈用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从柿子蒂下划一道口,手腕轻轻一转,橙红的果皮就像绸带似的缠在刀上,露出嫩黄的果肉,透着水润的光。
接下来的日子,院子里就成了柿饼的世界。竹竿架得整整齐齐,削好的柿子一个个用麻绳串起来,挂在竹竿上。阳光好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金灿灿的柿子,风一吹,柿子轻轻晃,像一串串小灯笼。晒柿子是个细活儿,不能急。白天要让太阳晒透,把水分慢慢抽走;傍晚得收进棚里,怕露水打湿了;遇上阴天,还得用柴火轻轻烘,火不能大,不然柿子会焦。妈妈总守在旁边,时不时翻一翻柿子,指尖碰一碰果肉,念叨着:“得等它软下来,像婴儿的脸蛋儿那样,才好捏。”
捏柿饼是最有意思的一步。晒到半软的柿子,果肉里的糖分开始往外渗,妈妈会把它们从绳上解下来,掌心托着,另一只手轻轻揉。不是使劲捏,是顺着果肉的纹理,一点一点把里面的硬块揉开,让糖分均匀地裹在果肉里。揉好的柿饼要再挂回去晒,等表面结出一层薄薄的白霜,就可以收进瓷缸里“回软”。瓷缸底下铺一层稻草,柿饼一个个码好,再盖一层稻草,封紧缸口。妈妈说,这是让柿饼“酿”出味儿来,等过个十天半月,开缸的时候,满屋子都是甜香,那才是最好吃的时候。
富平的柿饼,跟别处的不一样。它不是干硬的,是软乎乎的,咬一口,果肉绵密得像云朵,甜劲儿不冲,是慢慢渗出来的,带着点柿子本身的清香。最妙的是那层白霜,不是白糖,是柿子自己析出的糖霜,嚼起来沙沙的,中和了果肉的软,一口下去,又绵又沙,甜得刚刚好。小时候,我总爱趁妈妈不注意,偷偷掀开瓷缸的盖子,捏一个柿饼揣在兜里,跑到塬上的柿树下吃。风刮过树叶,簌簌地响,嘴里是柿饼的甜,手里还沾着白霜,那是童年最解馋的时光。
后来我来到陕北上班,也见过市场上的其他柿饼,总没有富平柿饼的韵味。刚刚刷视频看到了富平的柿子,熟悉的画面涌上心头,思绪被拉回到了老家院子——竹竿上挂着金灿灿的柿子,妈妈正眯着眼睛揉柿饼,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暖得像柿饼的甜。
富平的特产不少,有琼锅糖,有苹果,但唯有柿饼,像一根线,牵着我和家乡。它藏着富平的水土:秦岭挡住了寒风,让柿子能好好过冬;石川河的水滋养了土地,让柿树结出甜果。它也藏着富平人的性子:不急不躁,像晒柿饼那样,慢慢熬,慢慢等,才能酿出最醇厚的甜。每次吃起富平柿饼,就想起老家的塬,老家的柿树,还有妈妈的笑——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掉的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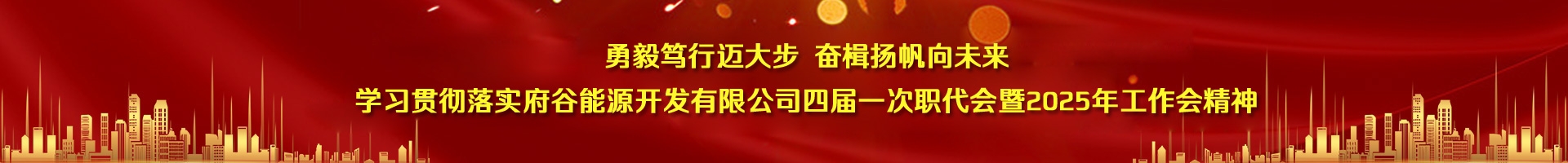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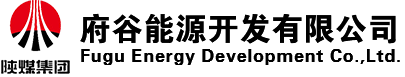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