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场秋雨后,村子里的风就带了凉意,可柿子树偏要和这冷意较劲儿——枝丫上的青果一夜之间就褪了涩,裹上橙红的衣裳,像无数个小灯笼,把村口到巷尾的路都照得暖融融的。这是我们村最热闹的时候,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盼头。

我家老屋门口就有两棵老柿树,树干粗壮结实,树桠歪歪扭扭地伸到屋顶,每年都结满果子。小时候,我总盼着霜降,不是因为能穿厚衣裳,是因为爷爷要摘柿子了。天刚蒙蒙亮,爷爷就扛着木梯架在树下,梯子腿裹着旧布,怕蹭坏树皮。他踩着梯子往上爬,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手里的竹篮挂在枝丫上,摘一个柿子就轻轻往里放,生怕碰破了果皮。“摘柿子摘得轻,就像捧着刚睡醒的娃娃。”爷爷的声音从树上飘下来,我蹲在树下捡偶尔掉落的柿子,指甲掐开一点皮,涩得直咧嘴,爷爷就笑:“傻丫头,这得等晒成柿饼才甜。”
摘完柿子,院子里就成了“柿子摊”。奶奶把柿子倒在青石板上,用井水一个个洗干净,再摆到苇席上晒。阳光好的时候,苇席上金灿灿一片,柿子的香气慢慢渗出来,引得蜜蜂嗡嗡转。我总爱趴在席边看,看柿子的表皮从橙红变成深红,再慢慢皱起纹路,像爷爷手上的老茧。有时候趁奶奶不注意,偷偷捏一个软的,咬一口还是涩,奶奶就点着我的额头说:“急啥?好东西都得等。”
等柿子晒得半软,就到了“做柿饼”的重头戏。奶奶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竹筐,手里握着铁皮刮子,从柿蒂往下一旋,橙红的果肉就露出来,黏糊糊的汁水顺着指缝流到手腕上,她也不擦,只偶尔在围裙上蹭一下。去皮的柿子要串起来挂在屋檐下的木架上,爷爷早把细麻绳剪成一段段,我帮着递绳子,看着一串串柿子垂下来,风一吹就轻轻晃,像极了过年挂的灯笼。等柿子晒得半干,就到了“捏饼”的时候。奶奶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捧着软乎乎的柿子,轻轻一捏,再顺时针转着圈揉,把果核揉到一边,果肉就变成了扁圆的饼状。我学着奶奶的样子捏,要么把柿子捏破,要么揉得不成型,奶奶就握着我的手教:“力道要匀,像哄娃娃睡觉那样轻。”捏好的柿饼要一层一层码在陶缸里,每层中间铺张油纸,缸口盖块粗布,让柿饼在里面慢慢“上霜”。
大约半个月后,掀开缸盖的瞬间,白霜的清冽混着果肉的甜香扑面而来。柿饼裹着厚厚的白霜,像撒了层白糖,咬一口,外皮脆爽,内里软糯,甜而不腻,带着阳光和风的味道。奶奶会把柿饼装在竹篮里,送给邻居和亲戚,巷子里的人见面都问:“你家柿饼上霜了没?”
后来我到城里读书,每年柿饼季,奶奶都会寄来一筐柿饼。拆开包装,白霜落在手心,咬一口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去年冬天,我带着孩子回了趟老家,院门口的柿子树还在,木架上挂着新晒的柿饼,奶奶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孩子蹲在树下捡落果,像极了小时候的我,妈妈站在木梯上,阳光洒在她和孩子身上,画面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如今,家乡的柿子沟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到霜降,来摘柿子、学做柿饼的人络绎不绝。妈妈的手艺也成了“非遗”,她教游客捏饼时,总说:“做柿饼和做人一样,要耐得住性子,等得起时间。”看着漫山的柿子红,我忽然明白,家乡的柿饼红的不只是果子,更是一代代人守着的手艺,是藏在时光里的乡愁,是无论走多远,一想起就觉得温暖的味道。
每次离开村子,我都要摘几个没晒的柿子带在路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往后退,手里的柿子暖暖的,我就知道,不管走多远,村子里的柿子总会红,家里的人总会等,这份甜,永远都在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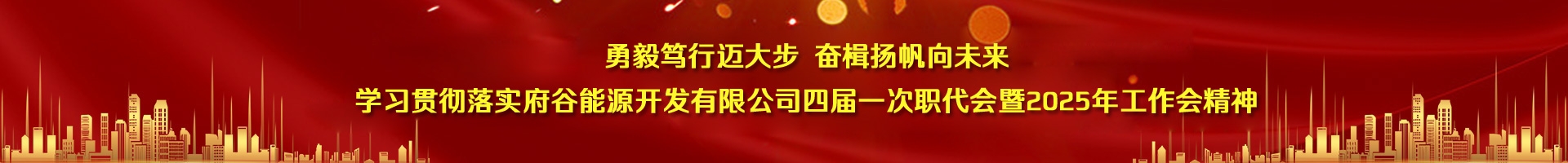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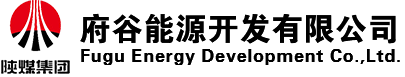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