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盘旋上山时,天是青灰色的,像一块未经打磨的巨砚。窗外的景致,已然是一幅褪了色的古画。那些在春夏里曾放肆过的草木,此刻都收敛了形迹,只余下些枯槁的、黄褐的底子,疏疏朗朗地铺展到视野的尽头。山石裸露着坚硬的脊背,上面仿佛凝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白气,那便是霜了。是了,今日霜降。这个节气,名字里便带着一股凛冽的、不容分说的寒气,仿佛一声冷静的宣告。

及至山顶,风陡然大了,呼啸着从四面八方涌来,带着一种纯粹的、金属般的凉意,直往人的骨缝里钻。而就在这片被寒风统治的山脊上,它们静静地伫立着——那些巨大的风机。
我从未在这样一个节气里,如此切近地观察它们。远望时,它们是现代工业的诗行,是洁白的、优雅的;但立于其下,才感到一种令人失语的庞大与沉默。那笔直的塔筒,是纯白色的,冷冽得像一根巨大的冰柱,直插灰蒙蒙的天心。而头顶那三片长得出奇的叶片,此刻竟是静止的。它们就那么静静地悬着,在青灰色的天幕上,构成一个极简的、充满几何之美的符号。这静止,比转动时更富有一种张力。仿佛一个巨人,在寒流中屏住了呼吸,积蓄着某种撼天动地的力量。
风更紧了一些,带着尖锐的哨音。终于,那巨大的叶轮,仿佛从一个世纪的沉睡中苏醒,极不情愿地、却又无可抗拒地,开始转动。起初是缓慢的,带着一种庄严的迟滞,像古老的石磨;随即,速度便快了起来,划出一个完整的、银灰色的圆。“呜——呜——”那声音并不刺耳,是浑厚的,低沉的,仿佛是从大地的肺腑深处发出的一声叹息。这声音与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竟不显得嘈杂,反而让这空旷的山野更显得寂静了。
我仰着头,看那巨大的阴影在头顶一圈圈地掠过,仿佛时间具象成了车轮。霜降的寒意,便在这规律的旋转与轰鸣中,被具象地切割着,转化着。古人于此时,见草木黄落,蛰虫咸俯,感受到的是自然的肃杀与收敛,是生命力的藏匿。他们围炉向火,将那一份寒气紧紧地关在门外。而我们,却在这至寒的时节,站在这山巅,将寒风本身擒获,将它那狂野的、足以摧折万物的力量,驯化成一缕缕光明与温暖,输送到远方灯火通明的城市里去。这是一种何等悖谬而又和谐的对立。
霜降,是秋的最后一次回眸,也是冬的第一次叩门。它介于收获与珍藏之间,介于喧闹与沉寂之间。而这些风车,不也正是矗立于这自然与人工、原始与文明边界上的巨人么?它们汲取着最古老、最原始的自然之力,却将它献祭给最现代的文明。
天色向晚,那青灰色的巨砚仿佛被倾入了浓墨,夜色开始浸润开来。山顶的风,愈发有了刀锋的质感。我准备下山了。回头望去,那些风车的轮廓在渐浓的暮色里已有些模糊,只剩那红色的航标灯,在每一座塔顶明灭闪烁,像一颗颗冷静的眼睛,又像为这沉入睡眠的、霜降的大地,所点亮的守夜的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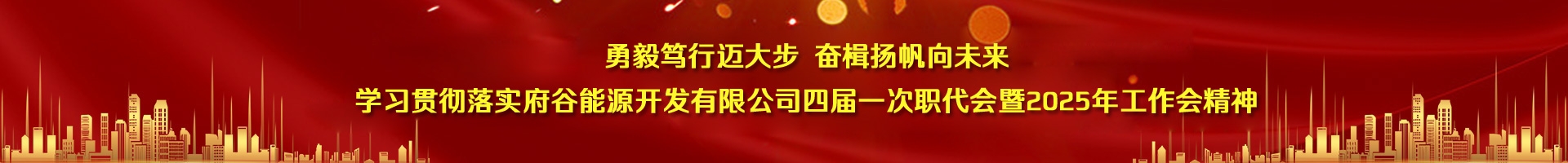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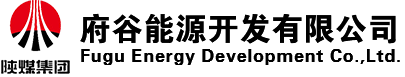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