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府谷,风里已裹着陕北特有的凉意,巡检完电厂的1#机组,望着窗外的远山覆着层淡雾静静铺展,忽然想起母亲前几天的电话——“家里花椒早摘完了,晒了满满的几大袋,等你回来给你装罐。”

算下来,我离开韩城到府谷工作,已有大半年没回家。往年这时节,正是家乡漫山遍野花椒红透的日子,也是家里最忙的时候。我们摘花椒,每人都要挎一个“笼”——那是用当地一种硬树枝条编的大篮子,分量不轻,形状圆鼓鼓的像灯笼,想来“笼”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韩城的花椒树多栽在坡地上,枝干上满是尖刺,我弓着腰走在前面,指尖捏着椒穗轻轻一拧,鲜红的花椒就簌簌落进笼里,还不忘回头叮嘱身后的妹妹:“慢点儿,别被刺扎着,摘不干净也没关系。”妹妹总点点头,小手攥着椒枝慢慢捋,虽不如我快,却格外仔细,笼里的花椒没一片碎叶。
父亲话少,闷头摘得又快又好,他的笼总比我们的先满。太阳升到头顶时,他蓝布衫的后背早被汗水浸出深色的印子,却还喊着“趁天好,多摘点,晒出来的椒才香”。等到夕阳把山坡染成金红色,我们的笼都装得冒了尖,我抢先把妹妹的笼接过来挎在肩上——她的笼虽没我的满,却也沉得勒肩膀,走几步就得换个肩。妹妹跟在我身后,时不时伸手帮我扶一下笼沿,轻声说“哥,我能自己挎”,我却笑着把她的手推开:“你还小,哥来就行。”一路走,一路都是笼里花椒散出的辛香。
回家后的活儿更不轻松。我家有两块房顶,父亲在前面弯着腰左右各揽一笼,我提着笼走在后面,踩着陡陡的台阶把花椒一笼一笼卸在房顶上,母亲和妹妹在下面递笼。妹妹手巧,还会把散落的花椒仔细捡进笼里,生怕浪费一粒;母亲则拿着木耙,在房顶上把花椒均匀铺开,每一块都要铺到。两块房顶铺完,天早就擦黑了,我揉着发酸的肩膀,父亲却还在检查有没有铺漏的角落,嘴里念叨着“花椒晒得匀,干得才快”。最让我们揪心的还是天气——要是傍晚看见西边云彩发红,全家人都要念叨“别下雨”;若是夜里刮起风,父亲总要爬起来去房顶看看,我也会跟着起身,帮着把被风吹得聚拢的花椒扒开。在韩城种花椒,从来都是靠天吃饭,每一粒花椒里,都藏着父母盼着好天气的心思,也藏着我护着妹妹收拾笼边碎椒的细碎暖意。
后来我到府谷工作,成了电厂的一名巡检员,每天打交道的是汽轮机的轰鸣声、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再难有机会帮家里挎笼摘花椒、替妹妹扛着重笼往家走。前几天视频,母亲说今年花椒收成好,妹妹长大了不少,自己能摘满一笼,还会帮着往房顶上递笼,就是父亲摘椒时被刺扎了手,硬撑着把最后几笼花椒扛上去,怕我担心一直没说。我看着屏幕里妹妹高了些的个头,忽然想起去年这时,我还和她一起把晒好的花椒从房顶扫下来,装进布袋,她踮着脚帮我扶着布袋口,母亲一边缝口一边说“等你稳定了,就把家里的椒寄点过去,让你在府谷也能尝到家里的味儿”。
府谷的风还在吹,心里却满是韩城的花椒红——满是尖刺的椒树、沉甸甸的笼、铺得满满当当的房顶,还有父母在夕阳下忙碌的身影,以及妹妹递来的那只扶着笼沿的小手。或许等忙完这阵子,我该回家看看,再挎一次那沉甸甸的笼,像从前一样帮妹妹扛着她的笼往家走,和她一起帮父亲翻晒院里的花椒,听母亲念叨今年铺房顶时,妹妹如何踮着脚把花椒递得又稳又准。那些藏在花椒香里的日子,是我在异乡最踏实的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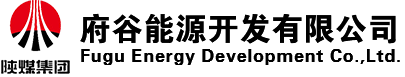
 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